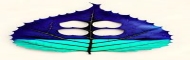闽南宝泉寺的格局,是和别处不同的:都是当山门一座巍峨的殿宇,殿后预备着斋堂,可以随时用斋。游山的香客,傍午傍晚下了山,每每花二十元,请一炷平安香——这是近些年的事,若在九十年代,只要五元——在殿前站着,匆匆拜了便走;倘肯多花五十,便能请盏莲花灯,供在佛前,若是布施到几百元,那就能在功德碑上留名,但这些香客,多是游客打扮,大抵没有这样虔诚。只有穿海青的居士,才踱进大殿东侧的禅堂里,捧经执杖,慢慢地坐禅。
我从二十岁起,便在寺里的客堂当义工。当家师说,样子太猥琐,接待不了方丈的贵客,就在外面照应些罢。外面的普通香客,虽然好说话,但唠唠叨叨问吉凶姻缘的也很不少。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自己的名字写到功德簿上,看过收据是否开错,然后才能放心:在这样严格的监督下,抽些香火钱也为难。加之我对那些中年妇女没有好脸色,所以过了几天,当家师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幸亏我姑母是寺里老功德主,辞退不得,便改为专管清扫藏经阁的闲职了。
我从此便整天的在藏经阁里,整理那些无人问津的经书。虽然没有什么纷扰,但总觉得有些沉闷,有些无聊。藏经阁主事的照法师是一副威严相,师兄们也没有好声气,教人活泼不得;只有觉法师来翻书,才可以笑几声,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觉法师是穿着僧袍却留着学士气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瘦高,青黄脸色,皱纹间时常夹些墨迹;一头剃得青茬茬的头皮,却总透着书卷气。穿的虽然是灰色僧袍,可是领口袖边都磨得发白,似乎十多年没有换新,却浆洗得干干净净。他对人说话,总是满口“阿毗达摩”“俱舍论”,教人半懂不懂的。因为他剃度出家时,师父给他起的法号叫“觉明”,大家就称他为觉法师。
觉法师一到藏经阁,所有看经的僧人便都看着他笑,有的叫道,“觉法师,你《大藏经》又读岔了页了!”他不回答,对经柜里说,“取一本《清净道论》,要巴利文版的。”便排出三本读书笔记。
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,“你一定又把唯识宗判为不了义了!”觉法师睁大眼睛说,“你怎么这样妄语诽谤……”“什么诽谤?我前天亲眼见你和净土宗的居士争辩,被骂得狗血淋头。”觉法师便涨红了脸,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,争辩道,“法义辨析不能算争……法义!……治学的事,能算争么?”接连便是难懂的话,什么“四谛十六行相”,什么“九心轮”之类,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:藏经阁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听人家背地里谈论,觉法师原来以仙游高考状元的身份考上北大,毕业后在某三流大学当了几年讲师,又不愿随俗;于是愈过愈迂,弄到要出家了。幸而英文底子好,便替寺里大和尚把那些鸡汤开示译成英语,换碗斋饭吃。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,便是好辩懒行。坐不到几天禅,便要和同修争论止观次第,如是几次,叫他共修的人也没有了。觉法师没有法,便免不了偶然说些狂慧的话。但他在我们寺里,品行却比别人都好,就是从不攀缘;虽然在藏经阁打印文件时偶尔没有现钱,暂时记在账本上,但不出一月,领了单金便会偿还,从账本上拭去了名字。
觉法师翻过几页经,青黄的脸色渐渐复了原,旁人便又问道,“觉法师,你当真懂梵文么?”觉法师看着问他的人,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。他们便接着说道,“你怎的连个佛学院聘书也捞不到呢?”觉法师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,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,嘴里说些话;这回可是全是“十八不共法”之类,一些不懂了。在这时候,众人也都哄笑起来:藏经阁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在这些时候,我可以附和着笑,照法师是决不责备的。而且照法师见了觉法师,也每每这样问他,引人发笑。觉法师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探讨法义,便只好向居士说话。有一回对我说道,“你读过佛学院么?”我略略点一点头。他说,“读过佛学院,……我便考你一考。阿毗达摩里,不善心所有几个?”我想,精神病一样的人,也配考我么?便回过脸去,不再理会。觉法师等了许久,很恳切的说道,“不能答罢?……我教给你,记着!这些名相应该记着。将来出家做讲经师的时候,要用。”我暗想我和讲经师的等级还很远呢,而且我们寺里讲经也从不提这些;又好笑,又不耐烦,懒懒的答他道,“谁要你教,不是一十四个么?”觉法师显出极高兴的样子,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经柜,点头说,“对呀对呀!……那善心所呢,有几种,你知道么?”我愈不耐烦了,努着嘴走远。觉法师刚用指甲蘸了茶水,想在桌上写字,见我毫不热心,便又叹一口气,显出极惋惜的样子。
有几回,几个小沙弥听得笑声,也赶热闹,围住了觉法师。他便给他们讲《法句经》,一人一句。小沙弥听完经,仍然不散,眼睛都望着他带来的饼干。觉法师着了慌,伸开五指将饼干盒罩住,弯腰下去说道,“不多了,我已经不多了。”直起身又看一看饼干,自己摇头说,“不多不多!多乎哉?不多也。”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。
觉法师是这样的使人快活,可是没有他,别人也便这么过。
有一天,大约是盂兰盆节前的两三天,藏经阁的照法师正在慢慢的整理账目,忽然说,“觉法师长久没有来了。还欠寺里三百块打印费呢!”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。一个看经的法师说道,“他怎么会来?……他精神出问题了。”当家师说,“哦!”“他总仍旧是辩经。这一回,是自己发昏,竟辩到北京佛协请来的长老那里去了。长老的开示,驳得的么?”“后来怎么样?”“怎么样?先写检讨,后来是关禁闭,关了大半月,再送去精神科。”“后来呢?”“后来确诊了。”“确诊了怎样呢?”“怎样?……谁晓得?许是被迁单了。”照法师也不再问,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。
盂兰盆节之后,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,看看将近初冬;我整天的靠着电暖器,也须穿上棉袍了。一天的下半天,没有一个香客,我正合了眼坐着。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,“请一本《南传阿毗达摩》。”这声音虽然极低,却很耳熟。看时又全没有人。站起来向外一望,那觉法师便在藏经阁门下对着门槛坐着。他脸上灰而且枯,已经不成样子;穿一件破旧僧袍,盘着两腿,下面垫个编织袋,用麻绳在腰间系住;见了我,又说道,“请一本《南传阿毗达摩》。”照法师也伸出头去,一面说,“觉法师么?你还欠三百块打印费呢!”觉法师很颓唐的仰面答道,“这……下回还清罢。这一回是现钱,书要精装本。”当家师仍然同平常一样,笑着对他说,“觉法师,你又和人辩经了!”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,单说了一句“不要取笑!”“取笑?要是不辩,怎么要吃药?”觉法师低声说道,“调伏,调,调……”他的眼色,很像恳求照法师,不要再提。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僧众,便和照法师都笑了。我找了书,递出去,放在门槛上。他从破僧袋里摸出五十元钱,放在我手里,见他满手都是墨水,原来他便用这手抄经的。不一会,他抄完目录,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,坐着用这手慢慢挪去了。
自此以后,又长久没有看见觉法师。到了年关,照法师取下账本说,“觉法师还欠三百块钱呢!”到第二年的浴佛节,又说“觉法师还欠三百块钱呢!”到盂兰盆节可是没有说,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。
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——大约觉法师已经往生了。
一九九八年冬,有闽南居士言曾在某精舍见一僧,人问法要,但喃喃“佛法真伟大”“戒律的规定像手术刀一样精细”,问其名号,唯以指画地书“阿毗达摩不善心所有一十四”。或云即觉法师,然终不可考矣。